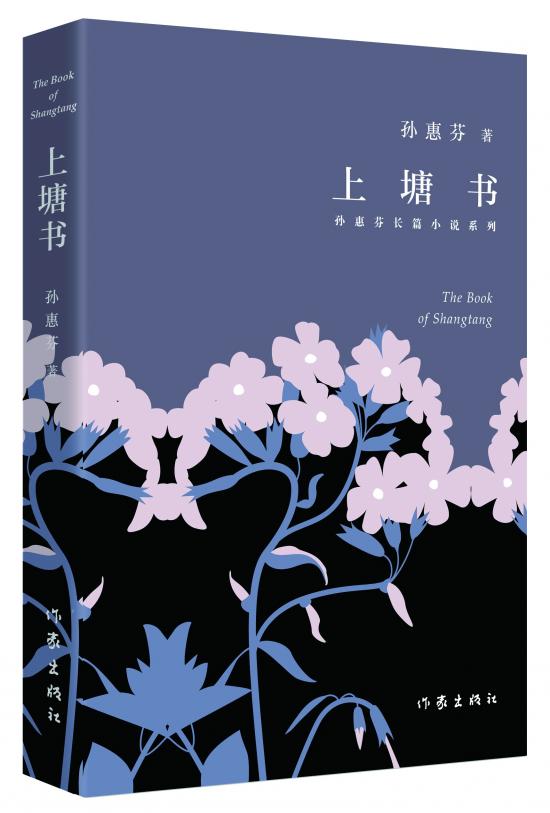我的创作生命中,一直以为《上塘书》是一部最为特殊的书。它的特殊,不在于它如何打破常规,把村庄当成人物、将人物嵌入村庄这个主角之下的叙事方式;也不在于它如何借用了地理、政治、交通、通信这些地方志语汇,打破以故事为主轴的结构,而在于它弥漫于语言缝隙的安详和平和,在于它将现实置入历史之中的叙事电影旁白一样的冷静和客观。
语言的安详,似乎来自创作者心态的安详,那是2003年,我进城7年,借助《歇马山庄》,那个被孤独淹没的落水者已经上岸。一方面,通过创作,我进一步确定了它是我唯一能够缓解孤独的朋友;一方面,孤独的暗礁一旦露出水面,不但不再可怕,而且还变成了赏心悦目的风景。露出水面的礁石变成风景,礁石也就在水面之上看到原来不曾看到的风景,那便是《上塘书》的全部——当我接受了孤独并能与之和平相处,“安详”不期而至。那情形,犹如坐飞机穿越乌云,蓝天之下,乌云变成了风景。只不过,那风景不仅仅是乌云的变幻,透过乌云,还看到了山川、大地、村庄,看到了村庄里正在发生的一切——冷静和客观,缘自观赏者自在的高度,缘自观赏者与被观赏者之间的距离,更缘自因高度和距离而获得的对于现实的想象。当观赏者像一个导游,凭借想象,引导游客进入村庄的时空,上塘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便发生了。
只不过,作为导游,我的情绪有些复杂,一方面,在拥有了一些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经历之后,我发现外部世界与记忆中的乡村有着本质上的相同,我想在一个封闭村庄里找到与外部世界的本质性联系;然而,正因为有了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经历,一直站在乡村城市化的变革之中,我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:记忆的乡村已经不在,那个上塘独有的精神世界,虽然有可能是外部生活的逆向延伸,那里的每一个人、每一条街道、每一种仪式,虽然无不与外面的世界发生联系,可是,当你把上塘当成一个生命对待,当你试图为她找到一个精神出口,你发现她正在经历荒芜与衰败……事实证明,是沟通的渴望铸就了创造。
生命的本质是创造,如同我们每一天里的创造。
《上塘书》出版后,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在一篇题为《〈上塘书〉的绝对理由》的文章里写道:孙惠芬写《上塘书》时面临的问题来自中国乡土的历史命运和美学命运,乡土已经处于城市的绝对宰制之下,它已经失去了经济上、伦理上和美学上的自足,这场历史巨变在小说艺术中一个意外但必然的后果就是——如果没有时间的庇护,如果你不把它放进记忆中的往昔,就绝不会有高密东北乡、马桥和呼兰河,小说家重绘世界地图的雄心在此意义上已告终结,乡土在中国现代以来小说传统中的中心位置也已终结,小说家变成了进城的民工,他们不得不在一个庞大的新世界中迷茫探索。
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迷茫探索,但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进城的民工,我在向城市的进发中,变成一个从孤独的深水里浮出水面的孤独的礁石,当我与孤独为伴,企图与它一起在写作中回望乡村,我的乡村却在消失……于是,《上塘书》的语调是审慎的、克制的,它不华丽,也不那么诗意——如果和萧红相比。萧红和莫言、韩少功的语调都有一种王者风范,他们说,事情是这样,那就是这样;而孙惠芬不,孙惠芬的姿态要低得多,她在叙述中似乎同时面对两个方向的挑剔,她似乎对上塘人说:是这样吧?她也对上塘之外的人说:是这样吧?这种叙述语调是孙惠芬从上述困境中发展出来的,她知道上塘不是中心,上塘人自己说了不算,所以她必须低调。她细致地观察上塘人生活的方方面面,她的目光悠长绵密,整部小说上百个人物,他们的生生死死,他们的疼痛、呼吸和战栗,都被体贴入微地述说着……《上塘书》是一本证明从此无“根”可寻的书。那个“根”已经不在了,孙惠芬的全部困难就在于她的这种现实感。
在此重温评论家的评论,我的心情十分复杂,就像当初写《上塘书》时面对乡村现实的复杂。十几年前,当貌似安详的状态覆盖了写作,满足于像一个导游一样向外面的人指指点点,并期待得到双向的沟通时,就连我自己都不曾知道,“无根”的现实感是如何压迫了我,影响了我……一晃十几年过去,再来打开《上塘书》的文字,才发现那所谓的安详里,处处隐藏着不安,那所谓的冷静与客观里,处处隐藏着因乡村消失而生出的犹疑、恐惧,由此,面对李敬泽先生当年对作品的诊断,以及在诊断中对写作者的理解、体恤,在感到羞愧的同时,又感到深深慰藉!
让我有同样感受的,还有一篇青年评论家于渺女士写的评论,她在题为《上有上塘村,下有曼哈顿》的文章里写道:
孙惠芬用了大量笔墨写了三条街之间扯不断的因缘和恩怨。她把家族辈分和社会阶层之间的争斗空间化了,这不是为了写起来方便,而是在揭示人类群体里另一种“村性”,那就是人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划出高低贵贱的阶层,而结果通常是在空间划分上展现出来……上塘世界隐藏着人类共有的“村性”,写作之前我不曾想过,可有评论者看出这一点,羞愧之中,令我无比欣慰!因为只要用心打量,就不难发现,所谓“村性”,正是暗礁的材质,它生成孤独,造成痛苦,它是人性的衍生品,同时,它也衍生沟通的渴望……
是为序。
(摘自《上塘书》,孙惠芬著,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)